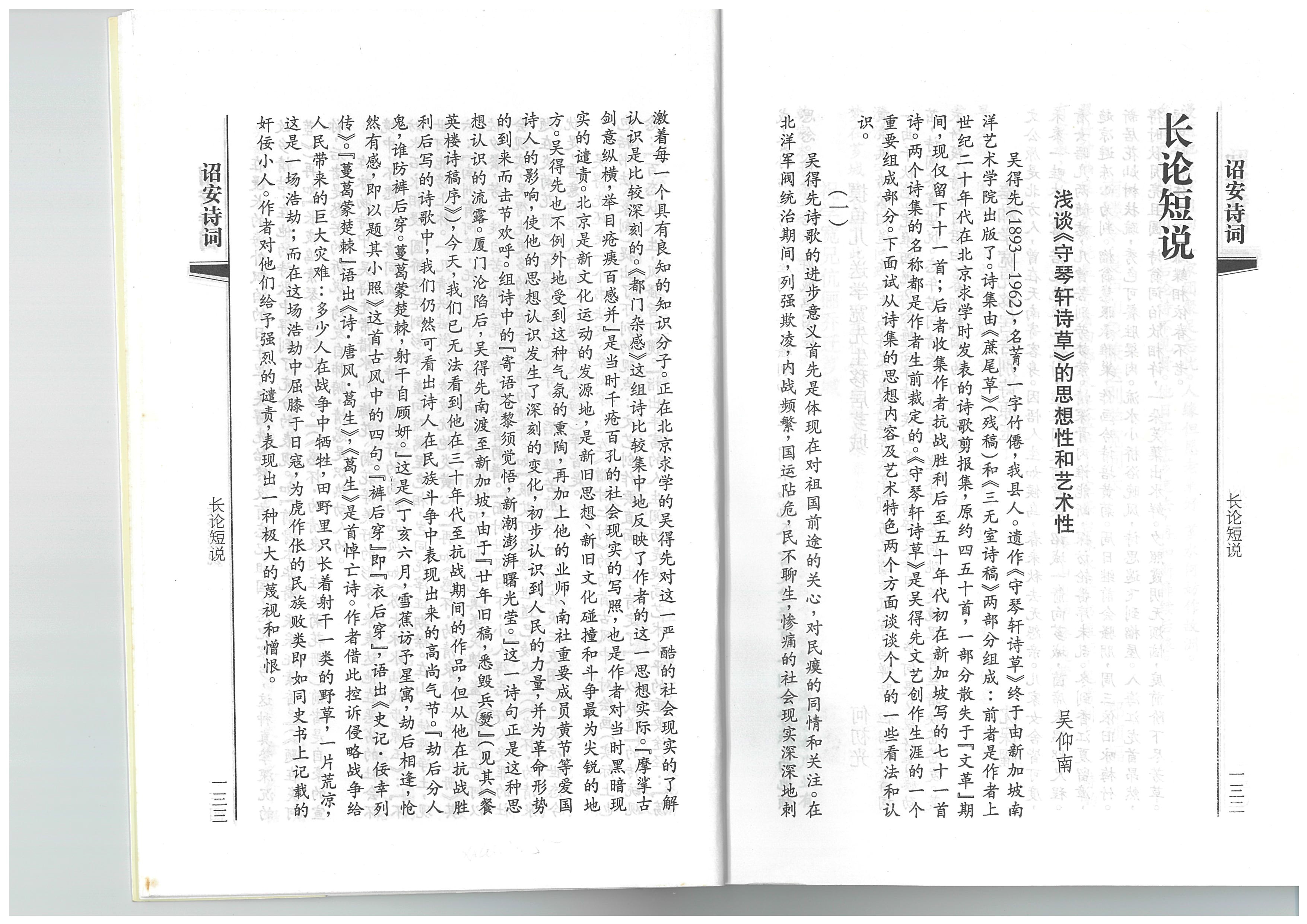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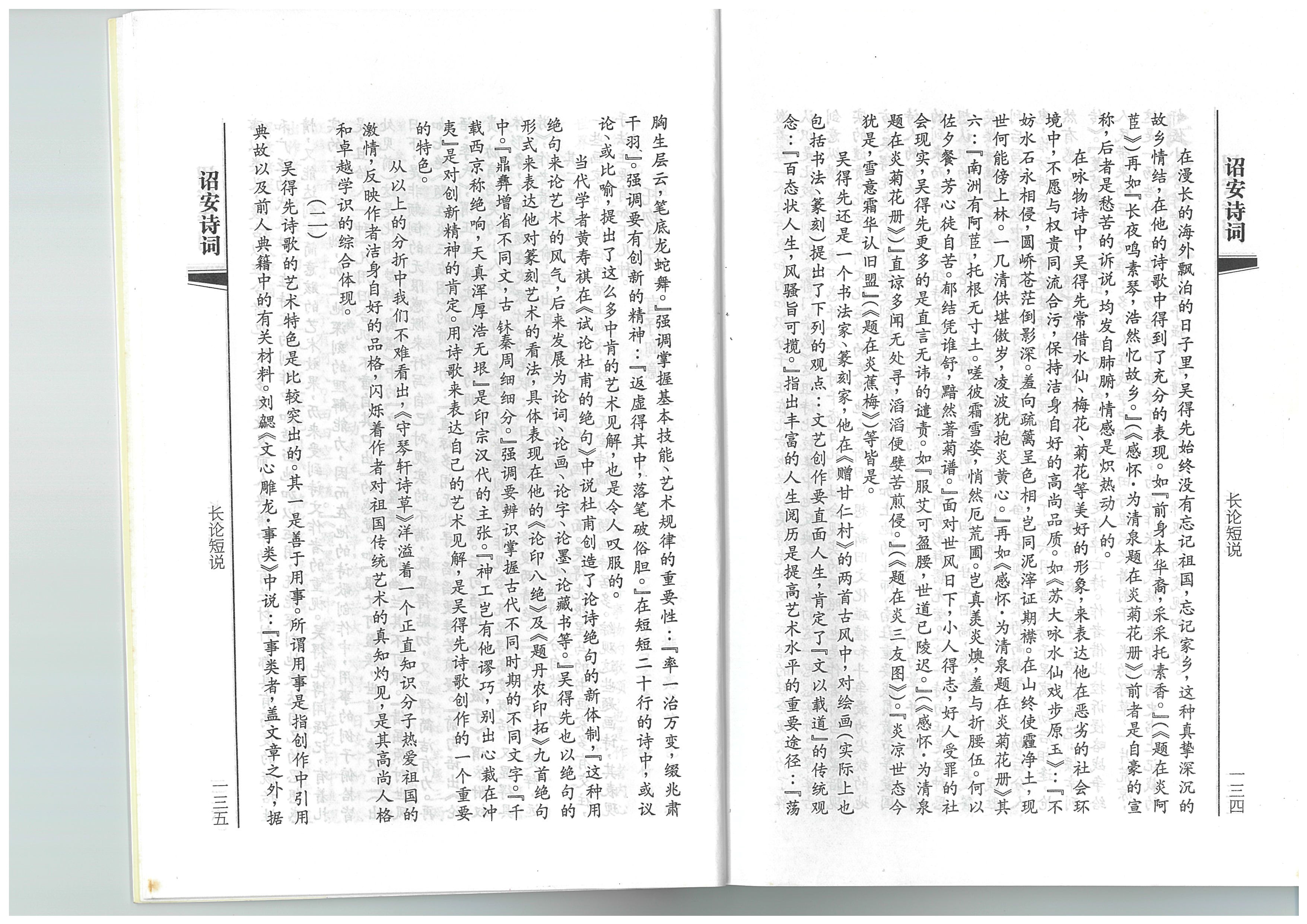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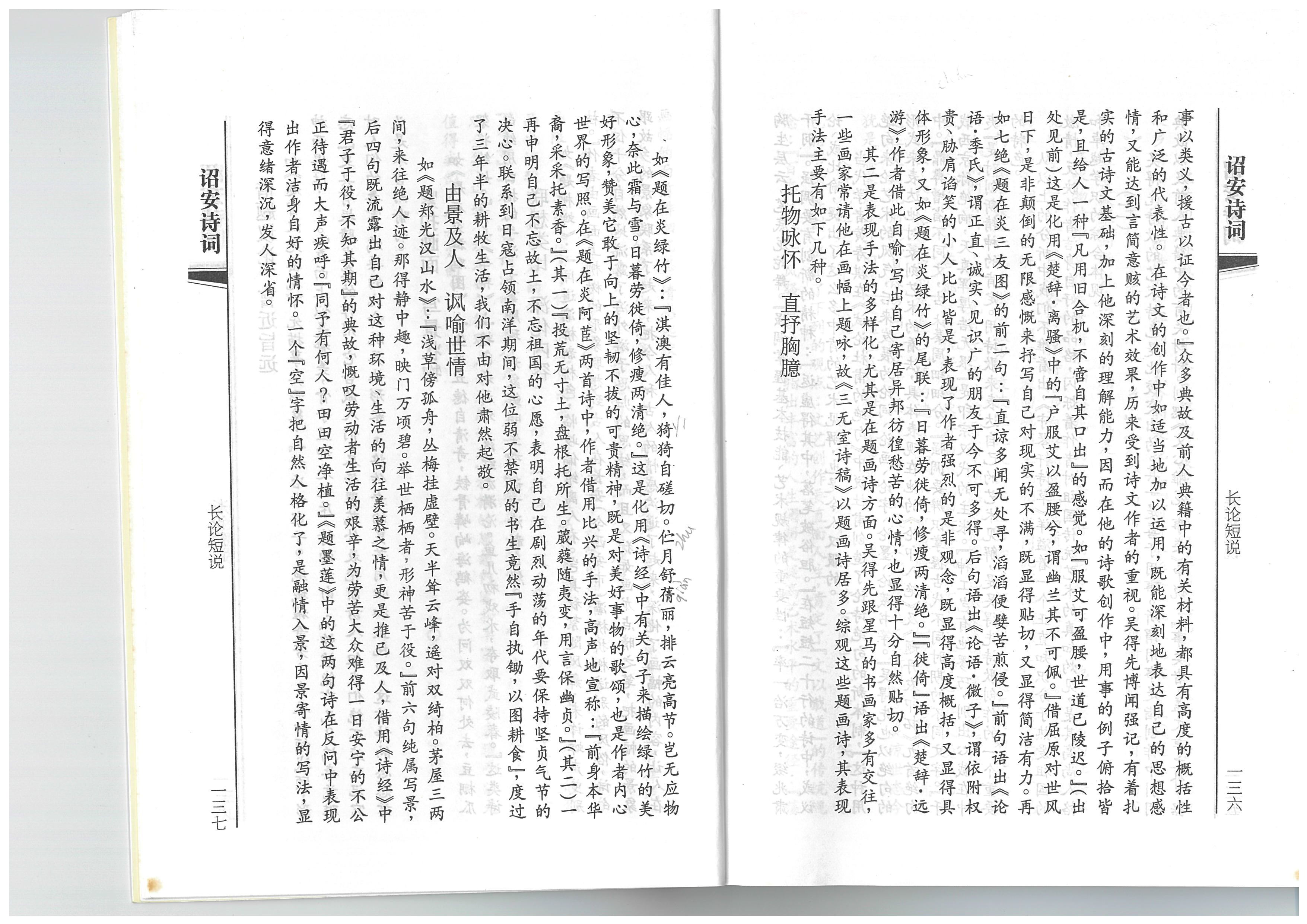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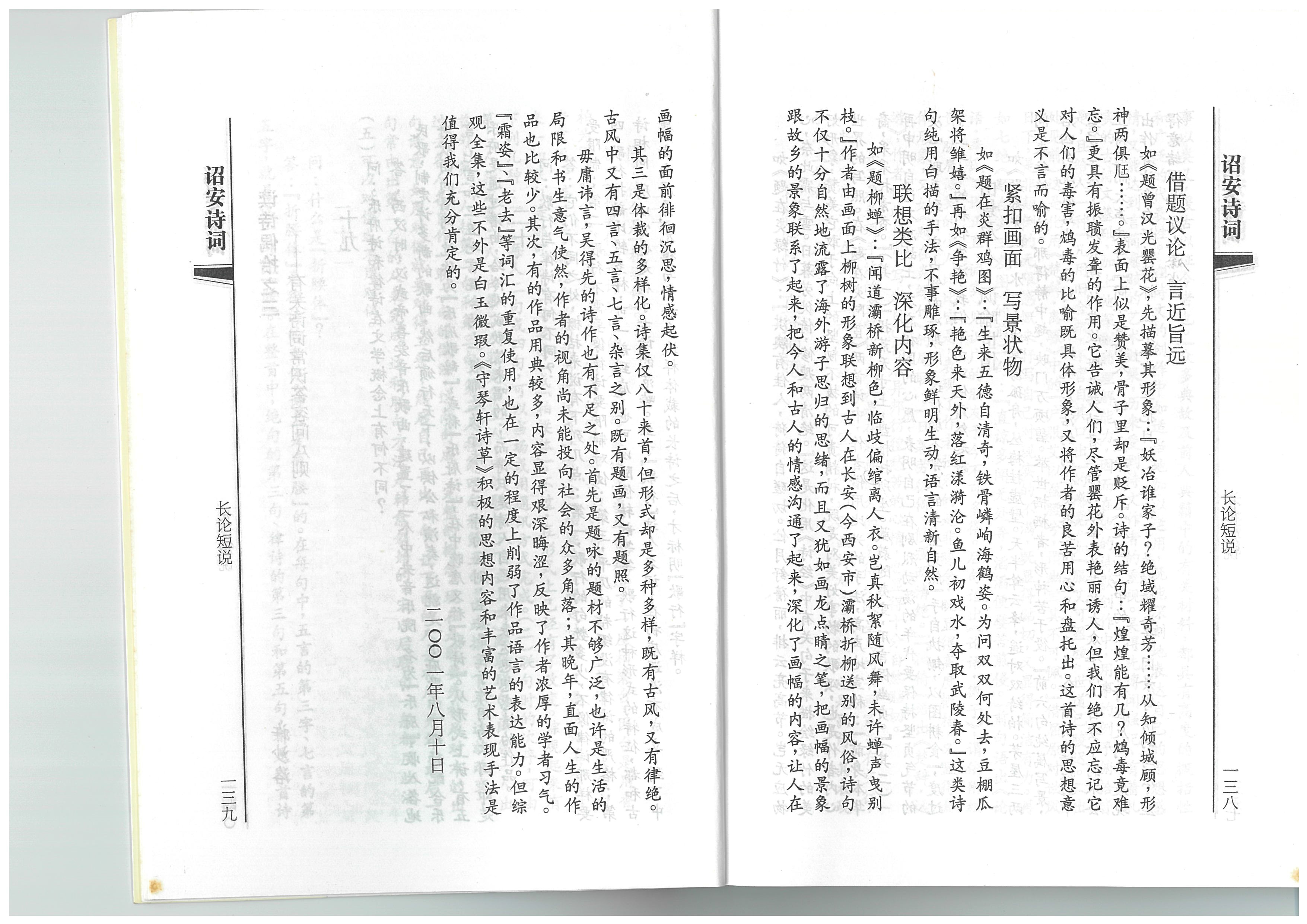
10/8/2001
《诏安诗词》第六集(第132页至第139页)
诏安县诗词学会出版 2002年
浅谈《守琴轩诗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吴仰南
吴得先(1893-1962),名育(艹字头),一字竹僊,我县人。遗作《守琴轩诗草》终于由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出版了。诗集由《蔗尾草》(残稿)和《三无室诗稿》两部分组成:前者是作者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求学时发表的诗歌剪报集,原约四五十首,一部分散失于“文革”期间,现仅留下十一首;后者收集作者抗战胜利后至五十年代初在新加坡写的七十一首诗。两个诗集的名称都是作者生前裁定的。《守琴轩诗草》是吴得先文艺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试从诗集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两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和认识。
(一)
吴得先诗歌的进步意义首先是体现在对祖国前途的关心,对民瘼的同情和关注。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列强欺凌,内战频繁,国运阽危,民不聊生,惨痛的社会现实深深地刺激着每一个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正在北京求学的吴得先对这一严酷的社会现实的了解认识是比较深刻的。《都门杂感》这组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这一思想实际。“摩挲古剑意纵横,举目疮痍百感并”是当时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的写照,也是作者对当时黑暗现实的谴责。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碰撞和斗争最为尖锐的地方。吴得先也不例外地受到这种气氛的熏陶,再加上他的业师、南社重要成员黄节等爱国诗人的影响,使他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初步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并为革命形势的到来而击节欢呼。组诗中的“寄语苍黎须觉悟,新潮澎湃曙光莹。”这一诗句正是这种思想认识的流露。厦门沦陷后,吴得先南渡至新加坡,由于“廿年旧稿,悉毁兵燹”(见其《餐英楼诗稿序》),今天,我们已无法看到他在三十年代至抗战期间的作品,但从他在抗战胜利后写的诗歌中,我们仍然可看出诗人在民族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高尚气节。“劫后分人鬼,谁防裤后穿。蔓葛蒙楚棘,射干自顾妍。”这是《丁亥六月,雪蕉访予星寓,劫后相逢,怆然有感,即以题其小照》这首古风中的四句。“裤后穿”即“衣后穿”,语出《史记·佞幸列传》。“蔓葛蒙楚棘”语出《诗·唐风·葛生》,《葛生》是首悼亡诗。作者借此控诉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多少人在战争中牺牲,田野里只长着射干一类的野草,一片荒凉,这是一场浩劫;而在这场浩劫中屈膝于日寇,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即如同史书上记载的奸佞小人。作者对他们给予强烈的谴责,表现出一种极大的蔑视和憎恨。
在漫长的海外漂泊的日子里,吴得先始终没有忘记祖国,忘记家乡,这种真挚深沉的故乡情结,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前身本华裔,采采托素香。”(《题在炎阿茝》)再如“长夜鸣素琴,浩然忆故乡。”(《感怀·为清泉题在炎菊花册》)前者是自豪的宣称,后者是愁苦的诉说,均发自肺腑,情感是炽热动人的。
在咏物诗中,吴得先常借水仙、梅花、菊花等美好的形象,来表达他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保持洁身自好的高尚品质。如“苏大咏水仙戏步原玉”:“不妨水石永相侵,圆峤苍茫倒影深。羞向疏篱呈色相,岂同泥滓证期襟。在山终使霾净土,现世何能傍上林。一几清供堪傲岁,凌波犹抱炎黄心。”再如《感怀·为清泉题在炎菊花册》其六:“南洲有阿茝,托根无寸土。嗟彼霜雪姿,悄然厄荒圃。岂真羡炎燠,羞与折腰伍。何以佐夕餐,芳心徒自苦。郁结凭谁舒,黯然著菊谱。”面对世风日下,小人得志,好人受罪的社会现实,吴得先更多的是直言无讳的谴责。如“服艾可盈腰,世道已凌迟。”(《感怀·为清泉题在炎菊花册》)“直谅多闻无处寻,滔滔便嬖苦煎侵。”(《题在炎三友图》)“炎凉世态今犹是,雪意霜华认旧盟”(《题在炎蕉梅》)等皆是。
吴得先还是一个书法家、篆刻家,他在《赠甘仁村》的两首古风中,对绘画(实际上也包括书法、篆刻)提出了下列的观点:文艺创作要直面人生,肯定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百态状人生,风骚旨可揽。”指出丰富的人生阅历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重要途径;“荡胸生层云,笔底龙蛇舞。”强调掌握基本技能、艺术规律的重要性;“率一治万变,缀兆肃干羽”。强调要有创新的精神:“返虚得其中,落笔破俗胆。”在短短二十行的诗中,或议论,或比喻,提出了这么多中肯的艺术见解,也是令人叹服的。
当代学者黄寿祺在《试论杜甫的绝句》中说杜甫创造了论诗绝句的新体制,“这种用绝句来论艺术的风气,后来发展为论词、论画、论字、论墨、论藏书等。”吴得先也以绝句的形式来表达他对篆刻艺术的看法,具体表现在他的《论印八绝》及《题丹农印拓》九首绝句中。“鼎彝增省不同文,古鉥秦周细细分。”强调要辨识掌握古代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字。“千载西京称绝响,天真浑厚浩无垠”是印宗汉代的主张。“神工岂有他谬巧,别出心裁在冲夷”是对创新精神的肯定。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艺术见解,是吴得先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特色。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守琴轩诗草》洋溢着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激情,反映作者洁身自好的品格,闪烁着作者对祖国传统艺术的真知灼见,是其高尚人格和卓越学识的综合体现。
(二)
吴得先诗歌的艺术特色是比较突出的。其一是善于用事。所谓用事是指创作中引用典故以及前人典籍中的有关材料。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众多典故及前人典籍中的有关材料,都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广泛的代表性。在诗文的创作中如适当地加以运用,既能深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又能达到言简意赅的艺术效果,历来受到诗文作者的重视。吴得先博闻强记,有着扎实的古诗文基础,加上他深刻的理解能力,因而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用事的例子俯拾皆是,且给人一种“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的感觉。如“服艾可盈腰,世道已凌迟。”(出处见前)这是化用《楚辞·离骚》中的“户服艾以盈腰兮,谓幽兰其不可佩。”借屈原对世风日下,是非颠倒的无限感慨来抒写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既显得贴切,又显得简洁有力。再如七绝《题在炎三友图》的前二句:“直谅多闻无处寻,滔滔便嬖苦煎侵。”前句语出《论语·季氏》,谓正直、诚实、见识广的朋友于今不可多得。后句语出《论语·微子》,谓依附权贵、胁肩谄笑的小人比比皆是,表现了作者强烈的是非观念,既显得高度概括,又显得具体形象,又如《题在炎绿竹》的尾联:“日暮劳徙倚,修瘦两清绝。”“徙倚”语出《楚辞·远游》,作者借此自喻,写出自己寄居异邦彷徨愁苦的心情,也显得十分自然贴切。
其二是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尤其是在题画诗方面。吴得先跟星马的书画家多有交往,一些画家常请他在画幅上题咏,故《三无室诗稿》以题画诗居多。综观这些题画诗,其表现手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托物咏怀 直抒胸臆
如《题在炎绿竹》:“淇澳有佳人,猗猗自嗟切。伫月舒蒨丽,排云亮高节。岂无应物心,奈此霜与雪。日暮劳徙倚,修瘦两清绝。”这是化用《诗经》中有关句子来描绘绿竹的美好形象,赞美它敢于向上的坚韧不拔的可贵精神,既是对美好事物的歌颂,也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写照。在《题在炎阿茝》两首诗中,作者借用比兴的手法,高声地宣称:“前身本华裔,采采托素香。”(其一)“投荒无寸土,盘根托所生。葳蕤随夷变,用言保幽贞。”(其二)一再申明自己不忘故土,不忘祖国的心愿,表明自己在剧烈动荡的年代要保持坚贞气节的决心。联系到日寇占领南洋期间,这位弱不禁风的书生竟然“手自执锄,以图耕食”,度过了三年半的耕牧生活,我们不由对他肃然起敬。
由景及人 讽喻世情
如《题郑光汉山水》:“浅草傍孤舟,丛梅挂虚壁。天半耸云峰,遥对双绮柏。茅屋三两间,来往绝人迹。那得静中趣,映门万顷碧。举世栖栖者,形神苦于役。”前六句纯属写景,后四句既流露出自己对这种坏境、生活的向往羡慕之情,更是推己及人,借用《诗经》中“君子于役,不知其期”的典故,慨叹劳动者生活的艰辛,谓劳苦大众难得一日安宁的不公正待遇而大声疾呼。“同予有何人?田田空净植。”《题墨莲》中的这两句诗在反问中表现出作者洁身自好的情怀。一个“空”字把自然人格化了,是融情入景,因景寄情的写法,显得意绪深沉,发人深省。
借题议论 言近旨远
如《题曾汉光罂花》,先描摹其形象:“妖冶谁家子?绝域耀奇芳……从知倾城顾,形神两俱尪……。”表面上似是赞美,骨子里却是贬斥。诗的结句:“煌煌能有几?鸠毒竟难忘。”更具有振聩发聋的作用。它告诫人们,尽管罂花外表艳丽诱人,但我们绝不应忘记它对人们的毒害,鸠毒的比喻既具体形象,又将作者的良苦用心和盘托出。这首诗的思想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紧扣画面 写景状物
如《题在炎群鸡图》:“生来五德自清奇,铁骨嶙峋海鹤姿。为问双双何处去,豆棚瓜架将雏嬉。”再如《争艳》:“艳色来天外,落红漾漪沦。鱼儿初戏水,夺取武陵春。”这类诗句纯用白描的手法,不事雕琢,形象鲜明生动,语言清新自然。
联想类比 深化内容
如《题柳蝉》:“闻到灞桥新柳色,临歧偏绾离人衣。岂真秋絮随风舞,未许蝉声曳别枝。”作者由画面上柳树的形象联想到古人在长安(今西安市)灞桥折柳送别的风俗,诗句不仅十分自然地流露了海外游子思归的思绪,而且又犹如画龙点睛之笔,把画幅的景象跟故乡的景象联系了起来,把今人和古人的情感沟通了起来,深化了画幅的内容,让人在画幅的面前徘徊沉思,情感起伏。
其三是体裁的多样化。诗集仅八十来首,但形式却是多种多样,既有古风,又有律绝。古风中又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之别。既有题画,又有题照。
毋庸讳言,吴得先的诗作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是题咏的题材不够广泛,也许是生活的局限和书生意气使然,作者的视角尚未能投向社会的众多角落;其晚年,直面人生的作品也比较少。其次,有的作品用典较多,内容显得艰深晦涩,反映了作者浓厚的学者习气。“霜姿”、“老去”等词汇的重复使用,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表达能力。但综观全集,这些不外是白玉微瑕。《守琴轩诗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2001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