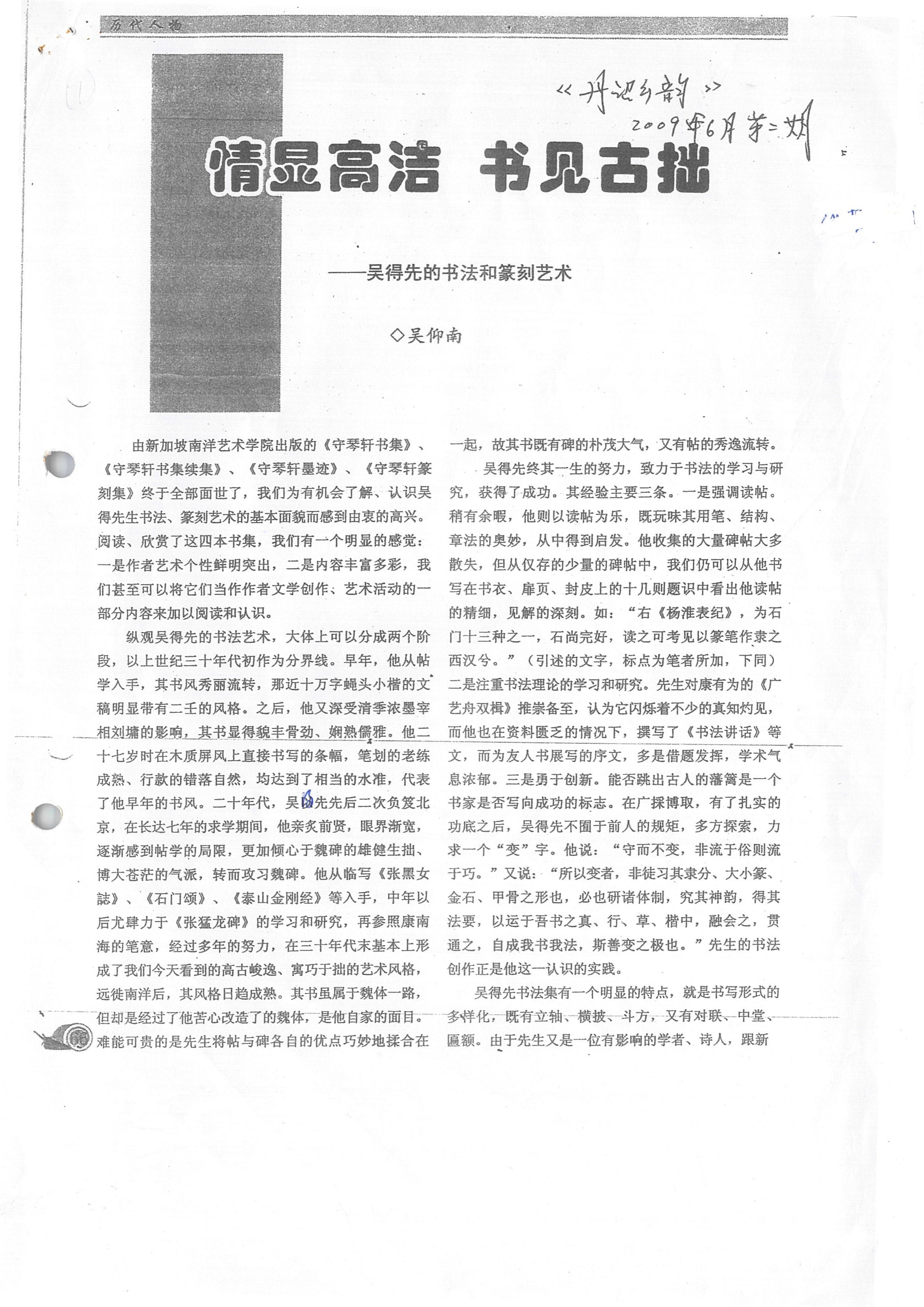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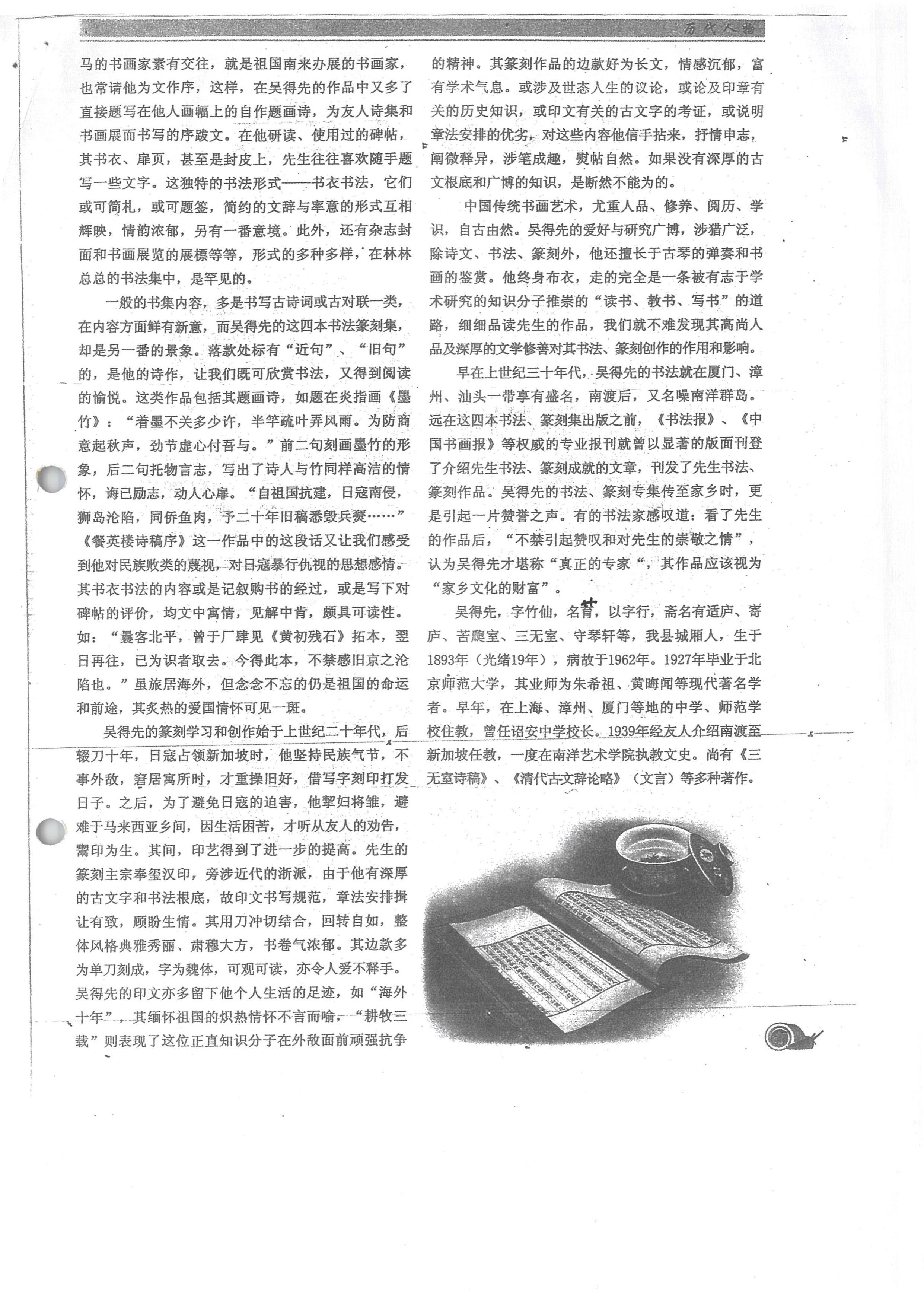
2009年6月
《丹诏乡韵》2009年6月第二期
情显高洁 书见古拙
——吴得先的书法和篆刻艺术
吴仰南
由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出版的《守琴轩书集》、《守琴轩书集续集》、《守琴轩墨迹》、《守琴轩篆刻集》终于全部面世了,我们为有机会了解、认识吴得先先生书法、篆刻艺术的基本面貌而感到由衷的高兴。阅读、欣赏了这四本书集,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感觉:一是作者艺术个性鲜明突出,二是内容丰富多彩,我们甚至可以将它们当作作者文学创作、艺术活动的一部分内容来加以阅读和认识。
综观吴得先的书法艺术,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以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作为分界线。早年,他从帖学入手,其书风秀丽流转,那近十万字蝇头小楷的文稿明显有二王的风格。之后,他又深受清季浓墨宰相刘墉的影响,其书显得貌丰骨劲、娴熟儒雅。他二十七岁时在木制屏风上直接书写的条幅,笔划的老练成熟、行款的错落自然,均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代表了他早年的书风。二十年代,吴得先先后二次负笈北京,在长达七年的求学期间,他亲炙前贤,眼界渐宽,逐渐感到帖学的局限,更加倾心于魏碑的雄健生拙、博大苍茫的气派,转而攻习魏碑。他从临写《张黑女墓志》、《石门颂》、《泰山金刚经》等入手,中年以后尤肆力于《张猛龙碑》的学习和研究,再参照康南海的笔意,经过多年的努力,在三十年代末基本上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高古峻逸、寓巧于拙的艺术风格,远徙南洋后,其风格日趋成熟。其书虽属于魏体一路,但却是经过了他苦心改造了的魏体,是他自家的面目。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将帖与碑各自的优点巧妙地揉合在一起,故其书既有碑的朴茂大气,又有帖的秀逸流转。
吴得先终其一生的努力,致力于书法的学习与研究,获得了成功。其经验主要三条。一是强调读帖。稍有余暇,他则以读帖为乐,既玩味其用笔、结构、章法的奥妙,从中得到启发。他收集的大量碑帖大多散失,但从仅存的少量的碑帖中,我们仍可以从他书写在书衣、扉页、封皮上的十几则题识中看出他读帖的精细,见解的深刻。如:“右《杨淮表纪》,为石门十三种之一,石尚完好,读之可考见以篆笔作隶之西汉分。”(引述的文字,标点为笔者所加,下同)二是注重书法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先生对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推崇备至,认为它闪烁着不少的真知灼见,而他也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撰写了《书法讲话》等文,而为友人书展写的序文,多是借题发挥,学术气息浓郁。三是勇于创新。能否跳出古人的藩篱是一个书家是否写向成功的标志。在广採博取,有了扎实的功底之后,吴得先不囿于前人的规矩,多方探索,力求一个“变”字。他说:“守而不变,非流于俗则流于巧。”又说:“所以变者,非徒习其隶分、大小篆、金石、甲骨之形也,必也研诸体制,究其神韵,得其法要,以运于吾书之真、行、草、楷中,融汇之,贯通之,自成我书我法,斯善变之极也。”先生的书法创作正是他这一认识的实践。
吴得先书法集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书写形式的多样化,既有立轴、横披、斗方,又有对联、中堂、匾额。由于先生又是一位有影响的学者、诗人,跟新马的书画家素有交往,就是祖国南来办展的书画家,也常请他为文作序,这样,在吴得先的作品中又多了直接题写在他人画幅上的自作题画诗,为友人诗集和书画展而书写的序跋文。在他研读、使用过的碑帖,其书衣、扉页,甚至是封皮上,先生往往喜欢随手题写一些文字。这独特的书法形式——书衣书法,它们或可简札,或可题签,简约的文辞与率意的形式互相辉映,情韵浓郁,另有一番意境。此外,还有杂志封面和书画展览的展标等等,形式的多种多样,在林林总总的书法集中,是罕见的。
一般的书集内容,多是书写古诗词或古对联一类,在内容方面鲜有新意,而吴得先的这四本书法篆刻集,却是另一番的景象。落款处标有“近句”、“旧句”的,是他的诗作,让我们既可欣赏书法,又得到阅读的愉悦。这类作品包括其题画诗,如题在炎指画《墨竹》:“着墨不关多少许,半竿疏叶弄风雨。为防商意起秋声,劲节虚心付吾与。”前二句刻画墨竹的形象,后二句托物言志,写出了诗人与竹同样高洁的情怀,诲己励志,动人心扉。“自祖国抗建,日寇南侵,狮岛沦陷,同侨鱼肉,予二十年旧稿悉毁兵燹……”《餐英楼诗稿序》这一作品中的这段话又让我们感受到他对民族败类的蔑视,对日寇暴行仇视的思想感情。其书衣书法的内容或是记叙购书的经过,或是写下对碑帖的评价,均文中寓情,见解中肯,颇具可读性。如:“曩客北平,曾于厂肆见《黄初残石》拓本,翌日再往,已为识者取去。今得此本,不禁感旧京之沦陷也。”虽旅居海外,但念念不忘的仍是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其炙热的爱国情怀可见一斑。
吴得先的篆刻学习和创作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后辍刀十年,日寇占领新加坡时,他坚持民族气节,不事外敌,窘居寓所时,才重操旧好,借写字刻印打发日子。之后,为了避免日寇的迫害,他挈妇将雏,避难于马来西亚乡间,因生活困苦,才听从友人的劝告,鬻印为生。其间,印艺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先生的篆刻主宗奉玺汉印,旁涉近代的浙派,由于他有深厚的古文字和书法根底,故印文书写规范,章法安排揖让有致,顾盼生情。其用刀冲切结合,回转自如,整体风格典雅秀丽、肃穆大方,书卷气浓郁。其边款多为单刀刻成,字为魏体,可观可读,亦令人爱不释手。吴得先的印文亦多留下他个人生活的足迹,如“海外十年”,其缅怀祖国的炽热情怀不言而喻,“耕牧三载”则表现了这位正直知识分子在外敌面前顽强抗争的精神。其篆刻作品的边款好为长文,情感沉郁,富有学术气息。或涉及世态人生的议论,或论及印章有关的历史知识,或印文有关的古文字的考证,或说明章法安排的优劣,对这些内容他信手拈来,抒情申志,阐微释异,涉笔成趣,熨帖自然。如果没有深厚的古文根底和广博的知识,是断然不能为的。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尤重人品、修养、阅历、学识,自古由然。吴得先的爱好与研究广博,涉猎广泛,除诗文、书法、篆刻外,他还擅长于古琴的弹奏和书画的鉴赏。他终身布衣,走的完全是一条被有志于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推崇的“读书、教书、写书”的道路,细细品读先生的作品,我们就不难发现其高尚人品及深厚的文学修养对其书法、篆刻创作的作用和影响。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吴得先的书法就在厦门、漳州、汕头一带享有盛名,南渡后,又名噪南洋群岛。远在这四本书法、篆刻集出版之前,《书法报》、《中国书画报》等权威的专业报刊就曾以显著的版面刊登了介绍先生书法、篆刻成就的文章,刊发了先生书法、篆刻作品。吴得先的书法、篆刻专集传至家乡时,更是引起一片赞誉之声。有的书法家感叹道:看了先生的作品后,“不禁引起赞叹和对先生的崇敬之情”认为吴得先才堪称“真正的专家”,其作品应该视为“家乡文化的财富”。
吴得先,字竹仙,名育(艹字头),以字行,斋名有适庐、寄庐、苦瓟室、三无室、守琴轩等,我县城厢人,生于1893年(光绪19年),病故于1962年。192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其业师为朱希祖、黄晦闻等现代著名学者。早年,在上海、漳州、厦门等地的中学、师范学校住教,曾任诏安中学校长,1939年经友人介绍南渡至新加坡任教,一度在南洋艺术学院执教文史。尚有《三无室诗稿》、《清代古文辞论略》(文言)等多种著作。
# 此文亦发表于2015年 一月份的《闽南风》